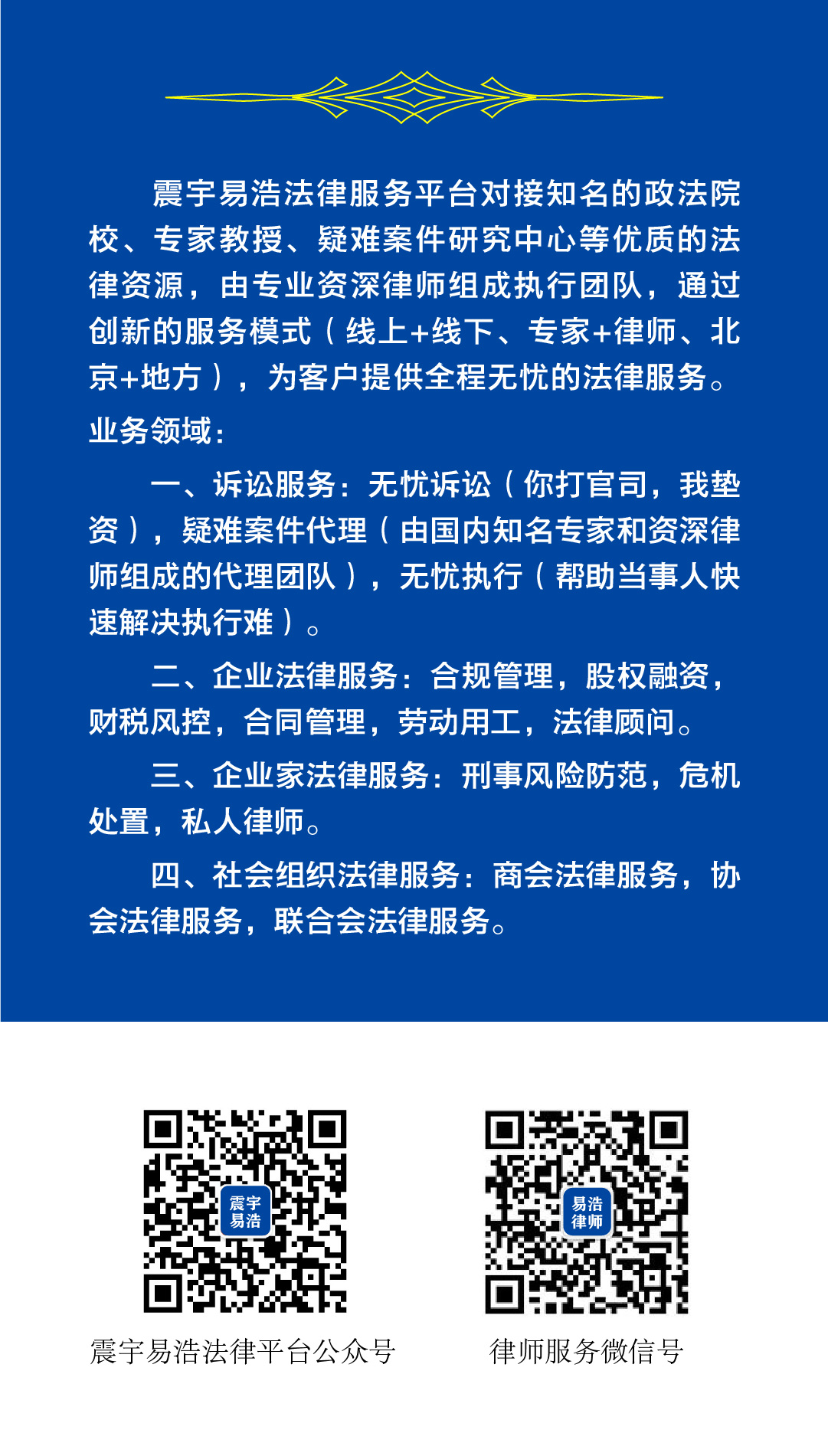
大数据杀熟:价格歧视经济学原理及合规考察
2021.06.23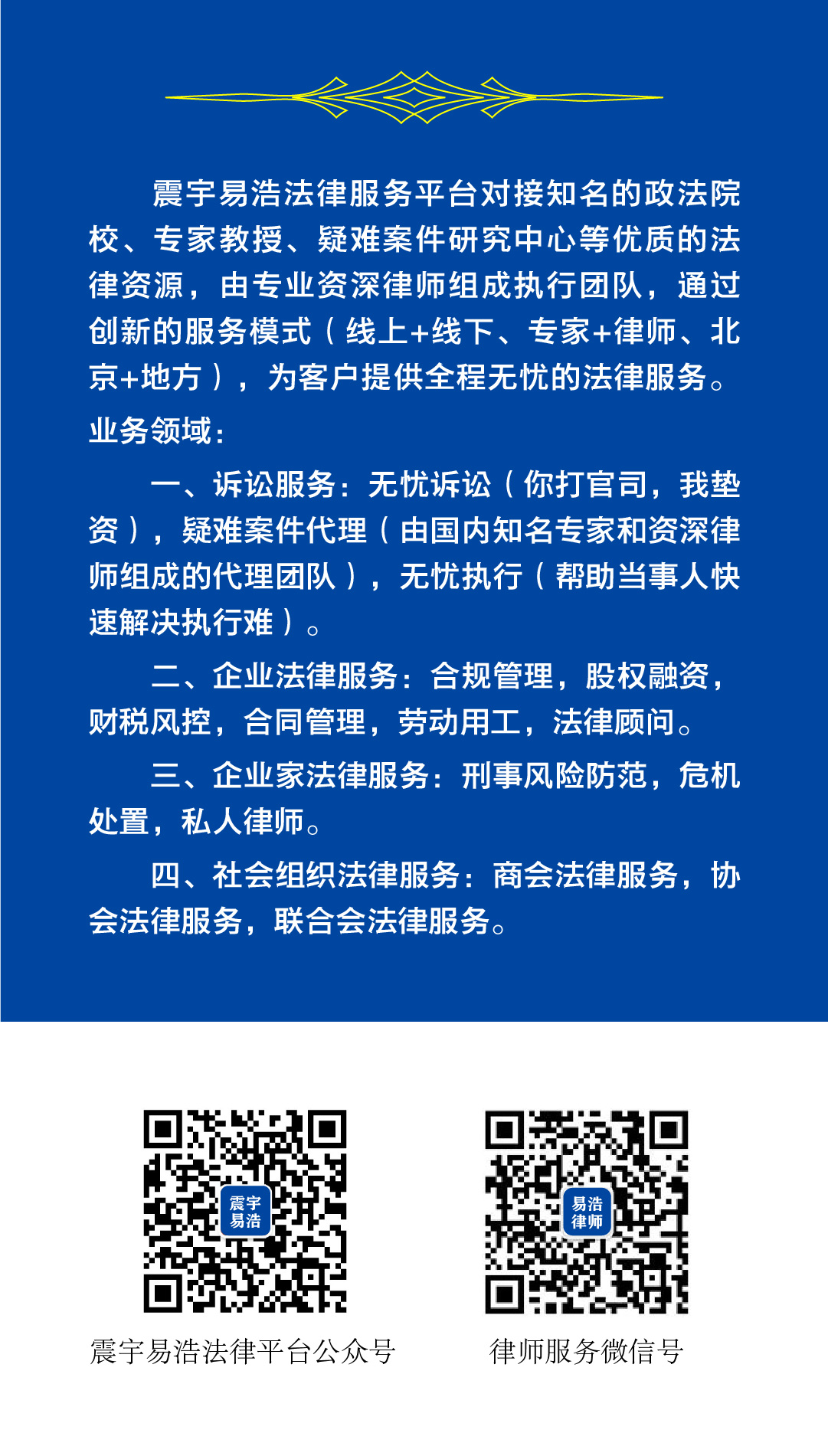
-

在线客服
-

在线留言
-

打赏我们
-

联系电话
联系电话
18611145206
-

小 程 序
手机扫一扫打开

-

回到顶部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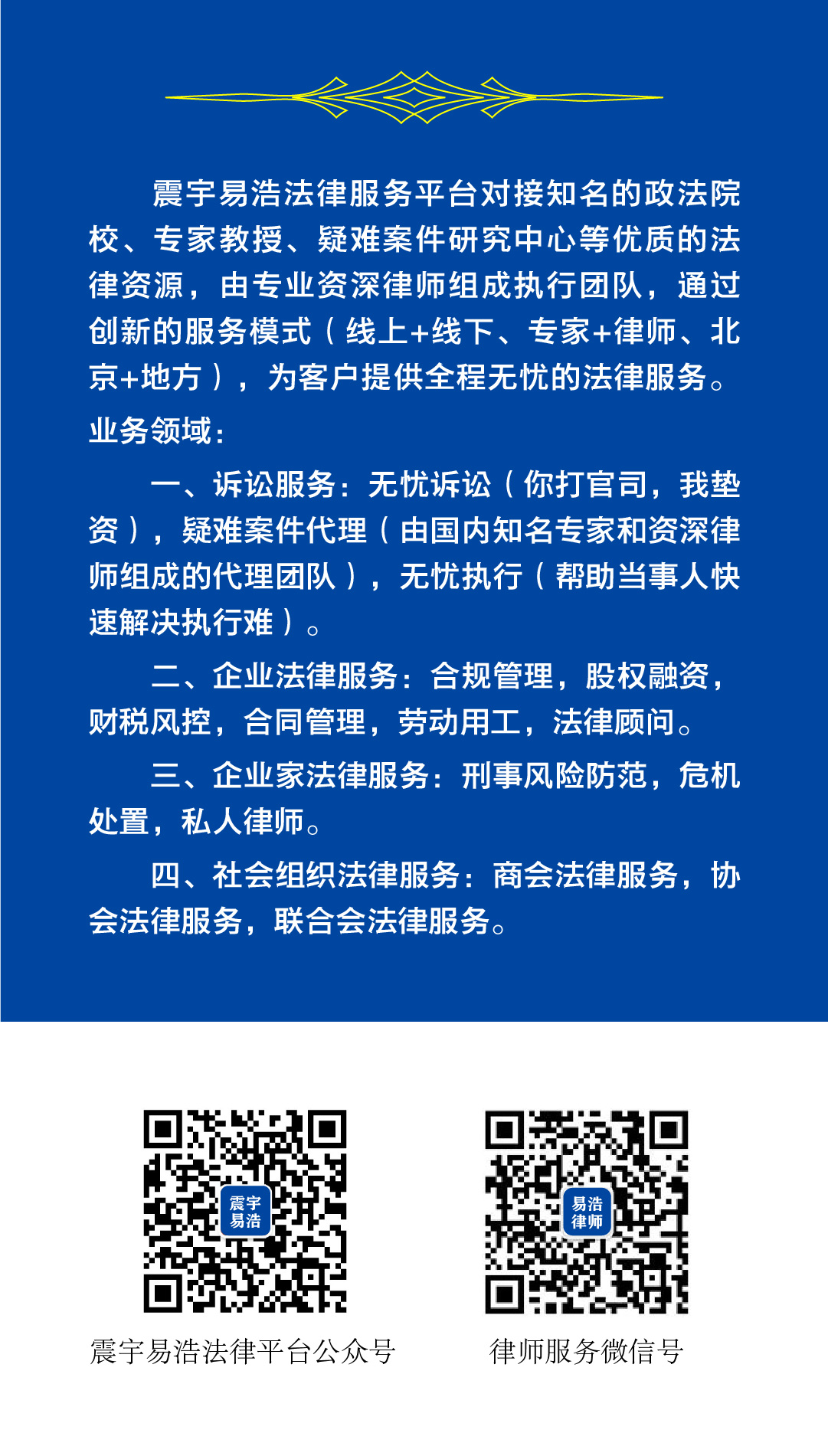




18611145206


